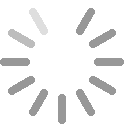非遗AB面:繁荣与危机
牟秉衡颤颤巍巍地站在台上,脸上还带着长途赶路后掩不住的疲惫。
在一场关于织造技艺的座谈会上,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竹帘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诚恳开口:“我做了一辈子竹帘,现在老了,精力不够了。我只希望更多有能力的年轻人能参与到梁平竹帘的设计、制作和传承里来,把这门手艺发扬光大。”
期盼新鲜血液的注入,恐怕是当下绝大多数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心愿。
数据显示,自2004年8月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已成为拥有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最多的国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名单已达3068人,但3068位传承人中50%以上超过60周岁。
“繁荣”与“危机”,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两面。A面是整个社会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愈发重视;B面则是作为个体的传承人日渐衰老,年轻人却因学艺周期长、经济回报低、未来成效难预测等原因迟迟不愿接过传承的重担。
解决了温饱,再来做风筝


把手艺当生活?宋长虹和父亲宋天亨,都是人到中年时才不得不面对的。不同的是,两代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做出的选择也大相径庭。
宋家的老屋在开封市私访院村,家里代代相传风筝制作手艺,父亲宋天亨是第五代传人。1986年,宋天亨所在的厂子因为效益不好,发不了工资。为了一家人的温饱,他拾起了祖辈传下的扎风筝手艺。
扎风筝挣钱,把手艺当生活,这是宋天亨给出的答案。第一年春天,他就得到了丰厚回报。“我们的风筝是‘象形’类,又是‘活骨架’,可拆卸、便携带,放飞时还无需助跑。”宋天亨回忆说,当时卖风筝的,全开封独他们一家,来家里买风筝的人,都快把小院的门槛踩倒了。
靠着卖风筝,宋家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然而这手艺,并不必然相承。2000年,宋天亨被诊断出双眼视网膜变性、白内障等眼疾,大夫说他很快就会失明。后来做了手术,模模糊糊还能看见,但风筝已经扎不下去了。一到晚上,他出门就得摸索着走。宋天亨想着把自家传了五代的风筝制作手艺交给一双儿女,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儿女的拒绝。
“如果我不去工作,跟你学扎风筝,那我吃什么喝什么?”
女儿宋长虹生性爽朗,拒绝父亲时也颇为直接。可望着父亲浑浊的双目和布满粗茧的双手,当女儿的最终还是松了口:“什么时候我不工作也饿不着自己了,再来跟你扎风筝。”
先解决温饱,再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放在传承手艺上,这是宋长虹给出的答案。在她看来,现如今做什么都比扎风筝挣钱快,她愿意扛起传承传统工艺的责任,但她希望父亲能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做好准备。
就这样,做了20多年销售工作的宋长虹选择在开封买房,当靠着房租能养活自己后,她回到私访院村的小院子里,从父亲手上接过了传承的重担。
不过,相比父亲守着小院亲手制作风筝,宋长虹的传承之路有些不同。她不再守着小院,而是通过参加电视节目、集会,开设风筝公益课程等方式,带着更多的人体验扎风筝的乐趣。
“一架纯手工的风筝,从劈竹子到扎骨架、糊、畫,整个过程需要20多个小时,售价在几百元以上,即使‘汴京宋室风筝’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即使我们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用来扎风筝,一个月的制作和销售数量也是有限的。”宋长虹说,“我发现,比起售卖成品风筝,把这门手艺用体验课的方式带给更多喜欢传统工艺的朋友和孩子们,让他们亲身感受民艺之美,似乎更有意义。”
这副担子,得交给有能力的人
非遗的传承重担,想接下并不容易。
与可以设定标准模式的机器不同,手工艺品的制作水准完全来自于手艺人的个人素养。即使用同样的原料、工序、技艺制作,老师傅和新学徒的成品仍有云泥之别。
“手艺,得‘守着’才能出艺。”在从艺60年的牟秉衡看来,手艺是一项磨手也磨人的工作,没有日积月累的经验累积,再有灵气的学徒也做不出真正的精品。
这些年,梁平竹帘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慕名前来学习的年轻人也逐渐增多,“有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来学做竹帘,学两三个月就走了,这样怎么能做出好东西呢?”
没有徒弟来学,令人担忧:有徒弟来学却不能坚持,更令人痛心。
今年,已经70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传承人康惠芳被联合国授予“文化大使”殊荣,拿了半个世纪针线的她,却时常因徒弟的问题焦虑。
在康惠芳的潮绣工作室里,最年轻的弟子也有40多岁。但是即使她们绣了这么多年,各有所长,能够掌握全面技艺的综合人才还是很少。
以康惠芳的经验来看,一个徒弟至少也要学习10年才能出师。“光是潮绣垫绣技法中,往绘制好的图样上垫棉花这道工序,就至少要练1~2年才能真正掌握。”
几年前,康惠芳从潮州的一家技工学校里招了十几个年轻学生,教他们学潮绣,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广东工业大学美术设计专业曾有一批学生来学习,康惠芳非常坦诚地告诉他们:“你们考上大学不容易,我们是实实在在用自己的双手创作作品,不是你们拍拍照、画画设计图就能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