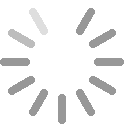我是一只冠冠雀(中篇)
第一章
一
我站在这座二十二层大楼前水磨石台阶上的时候,正是上午。
太阳光逼仄涌来,眼睛好一阵子睁不开。适应之后,开始打量着这座巍峨的建筑,突然产生了陌生之感,恍若隔世,今是昨非。出入这座建筑物二十年,真的还没有留心打量过它。现在,它敞开的门像个大嘴巴,黑洞洞的,刚刚把我吐出来,像吐出一团秽物。门前一个保安,背着手走来走去。年轻,胸脯宽阔肥厚,大概是刚吃了早饭的缘故,挺胸收腹,大公鸡般的傲然,几次经过我的面前,目光射向远方,一次也未与我相遇,好像我这个人并不存在。这才注意到,大门上方,有一排拓刻在水磨石上的新魏体:西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二十年我第一次发现它的存在。
我愧恧地收回目光。
二十岁大学毕业就成为了这个单位的一员。许多年来,给我发薪水奖金,逢年过节,还给我发许多福利品,鸡鸭鱼肉、清油大米、酱醋酒茶、海鲜山珍、各种水果,每逢生日,工会还让“爱心”蛋糕店给我送生日蛋糕,等等。虽然它没有给我评上高级地质师的技术职称,没有给我任命过什么科室长,或者哪个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也没让我担任过什么项目负责人,我呢,当然也没有在国家级学术刊物或者哪个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有分量的学术文章,给它增光添彩。尽管如此,我真的从心里感谢它。人要知恩图报是不是?我心里一声叹息:恩典,敝人自是记在了心里。图报也必须的,但是只有来生了。
我转过身,对着这座巍峨的二十二层大楼,和大门上方那排刻在水磨石上的字,恭敬地弯了一下腰,小声说了句,对不起。
年轻的保安这才注意到我,开始用警惕的目光向我瞄准。我对他报以和善友好的微笑,挥挥手,然后走下台阶。
二
我这年四十五岁。内退之后,我有了充足的理由自己支配时间。从前不大喜欢上班,从星期一开始,就盼着周末的到来。在属于自己支配的日子里,骑上自行车,去古河滩捡玉石,或者去湖畔垂钓。一个人走在古河滩上或是坐在湖畔,一天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我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不喜欢看电视,对电脑也不感兴趣,没有手机,也没有银行卡,好在结婚以来家庭财务一直由妻子管着。每天太阳不出我已出发,在早餐店买两个干馕,两块钱一个,装进布袋里,袋子里还有几根大葱,一袋榨菜,和一大壶水。在戈壁上骑着自行车,小路崎岖,自行车颠簸出如同秋天里的铃铛刺丛被大风吹过的声音。到了古河滩,把自行车放倒在一簇红柳旁,将装了一公斤半水的大水壶斜挎在身上,头上戴着麦秸草帽。直到太阳落下去,才骑上自行车返回。几日之后又去湖畔钓鱼。湖很大,水面生长着芦苇和蒲草,看上去湖对岸显得遥远。鱼很多,有时会竿竿不空,为了多在湖边安静呆上些时辰,我会像姜太公那样垂钓。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好像对古河滩和湖畔厌倦了。开始怀念起上班的日子,人真是很怪的动物。上班不可能了,只好整日蛰居在住所里。在黎明和黄昏之后,偶尔到门前的河边走一走。
三
我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太阳落下去之后,一个人躺在黑天鹅绒般的黑暗里,被河水的喧闹搅扰得难以入眠。卧床在临河窗户一侧,一扇窗不知何时悄然打开,夜风拂动厚重的帘布,流水的喧闹像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进入居所。起身关闭了窗户,帘布安静下来,抹去河岸照耀的灯光,也使喧闹声远去。我依旧躺在黑夜中,睡眠却像只迷途的羔羊,不知在何处徘徊。河水在低声地絮语,像一个人在我耳边讲述一段往事。
一个多月前,我被医生检查出患上了不治之症。我并不感到吃惊和恐慌,很平静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告诉我大概还有半年时间。我拒绝了医生要我住院治疗的建议,回到自己的居所。之所以把栖身之地叫居所,而不称之为家,是因为很长时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对它既不怎么眷恋也不深怀厌恶,而且一直想离开它,像一个人在夜到来之时与影子的告别,只是没想好去往何处。从医院回到居所,平静地重复着每个日子。早晨睁开眼,上半身离开床铺,坐一会儿,想一想曾做过什么梦。失眠使我的睡眠像块被老鼠偷食的蛋糕,本来已千疮百孔,却又被梦占去了很多。近一段时间以来,做了些奇怪的梦。看见自己又背上书包,去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又回到了大学的校园。同学们还是那样年轻,穿的衣服还是记忆里的样子。只有我是如今这副猥琐的小老头儿模样。醒来久久望着黑暗,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带着困惑离开了床,趿着拖鞋走进盥洗室,打开水龙头,撩起水轻轻敷到脸上,会瞥见镜子里那个憔悴的脸孔偷偷打量我。开始刷牙,白色的泡沫越来越多堆在镜中的嘴唇上。刮去胡须前小心地往脸上涂抹刮胡膏。疾病和岁月使这张脸日渐消瘦和衰老,眼神模糊不清,像仓储室里被遗弃多年的一页信纸,颊上红晕似乎还在,却变成铁板上的红锈。用刀具刮胡子,刮得小心翼翼。皮肤正在失去昔日的弹性,摸上去像橡胶,如我的神经一样开始脆弱,稍不小心就會被刮破。这一切做完之后带上门,楼梯间开始响起我的脚步声,很轻,怕惊动了谁。我去食堂用早餐。时候尚早,年轻人还在睡眠中,空旷的厅堂里回荡我一人的筷子碰到菜碟的响声。离开食堂返回居所。早晨的阳光将橘红色铺在弯曲的小道上,浓荫里没有晨风的吹拂,仿佛比居所还安静。一天中坐在居所那张黑皮椅子上,翻看一本本老旧的杂志,它们曾尘封在地下室的一只木箱里。更多时候我对着某本摊开的杂志发呆,上面刊有一篇小说,是我制造出来的,可是我对它们充满陌生感。只有到了太阳坠下地平线之后,夜的长翼完全覆盖了居所前的河流和岸上的树丛,我才走出居所到河岸边沿河行走。
一年多以前,妻子突然中止了与我的争吵。她去了遥远的新西兰,给女儿带孩子,并且一去不复返。她曾给我打来过电话,异国他乡的生活使她的心情有了很大的改变,她说做梦都没想到她这辈子还能过上如此美满如意的生活,她为后半生的好命运而欣慰,建议我是否也这样做。“不过,”她在电话里自顾自地叹息,“也许我的感觉不适用于你,你这人总是与众不同。”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十几秒钟,在没有听到我的回答之后,她悄然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