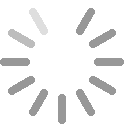我国传统诵读法的文章学价值
诵读不仅是语文阅读的重要方法,其在写作教学中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近些年,随着“经典诵读”的逐年升温,传统诵读教学也开始扭转近代以来的颓势,受到语文界乃至整个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诵读对于理解、品味经典诗文的作用,而对其促进书面表达的文章学价值缺乏应有认识,其在写作教学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在写作能力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传统诵读法进行重新审视,认识其文章学价值及其在写作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传统诵读法的历史演变
诵读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源远流长、地位尊崇,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古人注重口耳相傳的“声教”,“乐”成为声教的重要元素,这为诵读的产生积累了原始经验。据史料记载,早在《周礼》中就出现了“诵读”:“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1]这里的“讽”“诵”互通,指的就是诵读。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诵”既是一种能表现语气语调、韵律节奏的读法,也是一种寓景于情、以声传情的表现方式。尽管后来派生出吟诵、朗读等近似词语,但诵读诉诸声音的本义是不变的。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兴起,诵读诗歌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论语》中已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2]的说法,其中“诵”就是熟读成诵的意思。《史记》还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的记载,看得出孔子已经精于诵读并要求他的弟子也熟读成诵。由于诵读的方便易行,后来作为重要的读书方法代代相沿,备受重视。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经熟讲者,要妙乃见”“积累岁月,见道弥深”[4],意思是书读熟了才能懂得微妙意思,读得时间长了理解得才更透彻;《汉书》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5],可见诵读已成为当时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韩愈《进学解》中称自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6],可以看出“口勤”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作用。
而将诵读发展为一种重要教学方法的,则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朱熹提出读书有六法,诵读是其第一要诀。他在《蒙童须知》中说,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7]。他还主张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且这“三到”中以“心到”最为重要。当时人们对诵读的重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元代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里说:“每段要细读二百遍,默读一百遍,背读一百遍。”[8]即便除去夸张的成分,这在今天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到了明清两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快和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诵读这一古老的方法已渐露衰落的迹象,但人们对诵读的研究却没有止步。如王守仁根据儿童特点提出“口诵心惟,字字句句,演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9],其对诵读的论述已经触及学生的心理层面。不过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的语文教学已演变成科举制度的附庸,考试采取墨义、帖经、写经义文等形式,这就促使学生“死记经文,熟诵注疏”,诵读教学也在这种死记硬背中走进了死胡同。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择紧要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筋,所当切戒。”[10]从此讲授法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诵读则渐渐淡出了语文教学的舞台。即便今天的语文课程改革对诵读有所重视,但其地位与古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诵读的文章学价值及其在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各种形式的诗文诵读、经典朗诵活动接连不断。特别是2018年9月,教育部启动了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诵读工程”,这无疑将诵读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诵读在提升语文素养方面的作用正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但如果我们对诵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理解、品味和积累等阅读层面上,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其在语文课堂上的地位也难以得到有效巩固。因此,评估诵读在文章学、写作教学中的价值显得十分必要。
其实,在古代,人们早已认识到诵读对于写作的重要作用,所谓“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欧阳修语),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清人孙洙《唐诗三百首序》),等等。而十岁左右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十万言”“诵徘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陈思王植传》)的曹植,“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韩愈《进学解》)的韩愈,“昼课赋,夜课书”(白居易《与元九书》)以至“口舌成疮”的白居易,连如厕都要“讽诵之声琅然”(欧阳修《归田录》)的欧阳修等,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少年时代的勤苦吟诵。
但是以上多为经验之谈,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真正将诵读与写作联系起来考察,揭示诵读文章学价值的是清代桐城派的刘大櫆。他在传统“文气论”的基础上,从“养气”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因声求气”说,主张“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11]。刘大櫆强调通过诵读来感受文气、积养文气,认为熟到人我相通、化为己有时,就自然能写出好文章。之后的张裕钊对此作了补充:“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与古人沂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12]他注意到了诵读对于体味文章用意、文辞、风格、技巧方面的作用,较刘大櫆的认识更为全面、系统。但他们都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谈“养气”,“因声求气”也只是积养文气的重要方法,多少带有形式主义的色彩,至于诵读对写作的直接作用,他们均含糊其词,谈论得并不透彻。
诵读对于写作究竟有什么益处?概括起来说,诵读的文章学意义主要在于语感的培养和体式技法的化用上。我们知道,语感是人们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养成的一种直接、敏锐的感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并且语感只能在大量的言语实践中习得,主要包括吟诵、推敲、揣摩、分析和鉴赏等方式,其中诵读最符合语感生成的心理规律。从心理学角度讲,诵读是一种多功能的言语活动,既有视觉、听觉活动,还有发音器官参与其中,它通过眼、口、耳三条神经通道同大脑建立一种网状信号传递,其所形成的信号刺激强度以及使书面语系统内化的速度和牢固程度,要远远超过默读、谈论等其他言语方式。学生在诵读中不仅能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更能形成良好的书面语感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从而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