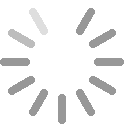史静寰:构建解释高等教育变迁的整体框架
“对教育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往往跟自己的学科是有联系的。”
“我本科学外语,硕士阶段学的是外国教育史,博士阶段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西方在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史静寰教授对教育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而进行的。有了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这两个基础学科的积淀,史静寰教授发掘出了从教育史和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教育问题的新途径,所以在教育研究上她有着独到的关注点和见解。
高等教育研究的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克拉克·科尔曾有一个基本的界定,他认为大学正处于“八个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危机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的会议上,也对这个观点有一个判断:“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实际上都处于危机之中。”所以“危机”几乎成为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现状的一个共识。2009年7月份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又用另外一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做出了界定:“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建立平等、多元的知识社会,发展研究、提升创造力与创新的主要力量。”这是从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对世界发展、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的角度所做的界定。
“无论是从危机的角度还是从重要性的角度,聚焦的都是高等教育研究怎样能够更好的贡献于这样一个时代,怎样去解读高等教育发展当中遇到的内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并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做高等教育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史静寰教授语。
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问题导向的特点,这是在高等教育研究界得到普遍认同的。特别是在中国,没有现成的模式供套用,所以高等教育的研究必须要从问题切入。“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问题导向’的特点,但研究的本质要求超越就事论事的描述和分析”史教授说,如果高等教育研究,仅仅是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那还远远没有达到研究的层次。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它的研究应该超越问题层次,不能仅仅就事论事的提出见解,而要有一个更普遍性的意义,所以,“一定要关注怎么样把经验层面的东西提升到学科普遍意义”。
构建框架的意义何在?
现今的高等教育研究一般都是从问题入手,也就是所谓的实证研究,那么对于实证研究来说,构建一个整体的解释框架,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哲学分析注重概念、范畴、命题等,强调理清概念的形成、内涵、本质。”史教授说,“其实它是用这样的概念、范畴、命题,构建起一个分析具体问题的逻辑系统。”所以在哲学研究中,非常注重这些基本的分析,通过基本的分析来反映思想变迁的路径。
史静寰教授表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非常注重构成‘社会’的要素、强调揭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框架的定义,是把一些表面看来可能不搭界的要素放在一起,从而揭示出它们内在逻辑上的一些关系。因此,框架很重要,框架可以简洁、明晰地抽象并呈现要素(概念);显示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要素相互作用及影响的方式等。柯林斯的“学术网络”“学术共同体”等既是概念,也是框架,揭示出“知识”的特性。教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也要关注构成社会的要素。因为教育是社会特征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反映,所以研究教育也要研究关系,研究构成要素,研究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及变化等,所以框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
高等教育变迁的本质是什么?
“影响高等教育变迁的核心要素都有哪些?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这一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的?”史教授的研究中曾针对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变迁的本质是什么?”
理论框架的构建有两个步骤:首先是从具体现象抽象出普遍概念(要素)。伯顿·克拉克在撰写其著名的《高等教育制度:学术组织的跨国比较》一书中指出:“要揭示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要素,就需要构建起‘通用型框架’”。康德的“范畴”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也都对此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然后是在要素之间建立起联系。要做到这点,就要在历史的框架内研究教育,“只有在过去当中,才能找到组成现在的各个部分”,“我们必须把自己移送到历史时间刻度的另一端”,“追随它所历经的、与社会本身的变化同步的一系列变化,直至最终到达我们当前的处境”;在社会的情势中研究教育,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想真正理解任何一个教育主题,“都必须把它放到机构发展的背景当中,放到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在区别教育体系、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分析教育,认识教育的“内在发展逻辑”, 不受人限制的“自发的机制”。教育制度是“明确、固定的安排”,教育观念是内在的价值观,观念与制度合在一起构成既稳定、又有变化的教育体系。(引自《教育思想的演进》)
高等教育研究界已有了诸多的经典解释框架,如布鲁贝克“二基础模式”、伯顿·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克拉克·科尔的“对抗三角形”、范富格特的“三角四块模式”。
在布鲁贝克看来,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动摇了二元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他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高深学问”一章中提出,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认识论为基础和政治论为基础。并列专题“实用主义基础”,认为“把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结合到一起的最好途径,是重新探讨当前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价值自由的认识论基础主要是现实主义。”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在世界普遍存在,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是理解世界高等教育整体和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越是抽象的理论越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因此,一个好的理论框架应该能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不同制度形态及其演变过程具有解释力。伯顿·克拉克从高等教育自身的制度形态、从大学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基础,提出的由国家权力、学术权力和市场力量三要素构成的经典三角形已成为解释现代高等教育系统运作、特别是进行多国高等教育体制比较时使用的经典模式。
克拉克·科尔认为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之后正处在“八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危机时代”。危机是由于构成高等教育的传统受到两大浪潮的冲击产生的,这两大浪潮代表了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两大需求:更平等的机会与更优异的能力。大学代表了积累的传统,平等与优异作为两大浪潮的主题,体现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在传统与现代需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也存在着相互间的互动与影响。
伯顿·克拉克和克拉克·科尔的模式不仅使高等教育变迁与社会环境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突出了高等教育系统和制度自身在应对社会变迁时所具有的主体性和复杂性。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要回答如何通过努力,使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各要素之间形成平衡与稳定,使高等教育系统在复杂的社会组织中更具活力,政策的作用与重要性得到凸现。范富格特运用整体论分析框架研究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特点,在伯顿·克拉克“协调三角形”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角四块模式”。此模式在认可政府作用的基础上,论证其作用的复杂性,将介入的结果与介入的方式和领域结合起来;论证大学是一个强有力的实体,强调教授及其组织的影响力;分析了市场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作用;独特之处是对几种力量的作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论证了“中介机构”作为缓冲组织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