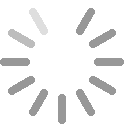晚清民初教科书变革与学生社群的兴起

摘 要:晚清民初政权更迭导致了教科书的变革。把教科书作为一种比报刊更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讨论了教科书出版与学生社群兴起的关系,从晚清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教科书内容角度,对一些常见的观点进行辨析,论述了晚清民初教科书的变革如何为五四学生运动提供了知识准备。
关键词:晚清民初 教科书 变革 学生社群 五四运动
中国古代除少数官学外,学校所用教材没有一定的体系,既无学制限制,亦无教法要求,更无审定教材的机构和组织。清末废科举、改书院、兴学堂、倡实学的教育改革和普通中小学教育的迅速扩展,直接推动了编译西方教科书热潮的兴起和民间自编教科书风气的形成。
新型教科书是学生最普通、最基本的读物,在清末民初的学生阅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教科书内容和语言方式的变化,会影响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与表达方式,进而关涉语言风格与时代风貌。特别是在清末民初时期,教科书通常是平民子弟唯一的读物,很多知识和体验都来自教科书,如同黎锦熙所言,“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须知这些书的势力,把二十多年以来青年们对于本国文字与文学的训练,和关于本国文化学术的常识,都给支配了:这是他们必须而有仅读的书,简直是去从前‘四书五经’的地位而代之。”
教科书不仅是教育产品,更是一种比报刊更有力、范围更广的传播媒介。从品种上讲,教科书不如报刊多,例如,在五四运动前,光白话报刊就有140多种,通俗白话小说更多,据统计,仅1900~1919年,长篇通俗小说就有500多种,但是,教科书的种类虽大大少于报刊书籍,它的发行量却是巨大的,例如,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元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在十五年中共印了2500版。从1907~1909年三年间全国新式教育发展状况(如表1),我们也可以大致推知教科书的发行量(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教科书)。
清末编辑教科书的官方机构是1906年成立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编译图书局制定的《编译章程》规定:“编纂教科书,宜恪守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室之宗旨;每编一种教科书,须兼编教授书;凡编一书,预先拟定年限
终点。”由于全国学堂的门类繁多,所需教材种类繁杂,不可能在短期内由官方包办,因而学部管理教科书的主要方式还是审定民间自编的教科书。1906年4月,学部公布了《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凡例》和《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凡例》,正式向全国公开审定教科书的标准和要求:(1)“凡本部所编教科书未出以前,均采用各家著述先行审定,以备各学堂之用”,其标准以学制为依据,以教育宗旨为指导。(2)审定程序为:教科书内容应以《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初等和高等小学科目为准;要求审定者须提出申请,并注明作者、出版年月、价格、印刷和发行单位;审定过的教材不准再行加价;已审定的教科书准其四至五年内通用。(3)学部对教科书的审定发行具有绝对管辖权,准予发行的书籍须标明学部审定字样,“如未经本部审定而伪托名者,应行查办”。(4)提倡鼓励改良教科书。颁布审定书目后,“如有佳本续出,竞争进步,当次第续行审定,随时发布”;各学堂在审定书目颁布前已使用的教科书,如不在书目之内,应送呈学部审定,
如已为善本,可继续使用。通过这些规定,学部将教材的内容审定权掌控在手中。而且,在学部的审定中,政治标准始终居于重要位置。1908年学部在审定何琪编的《初等女子小学国文》时,发现书中取材有“平等”字样,不仅不予采用,还查禁取缔。同年文明书局出版麦鼎华所译日本人著的《中等伦理学》,“学部谓中西学说杂糅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谬,下令查禁。”
民国时期,除了立即禁用前清教科书外,对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也进行了改革。1912年9月13日,
教育部颁布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主要内容包括:初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唯须呈请教育部审定;所编教科书,“应根据《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图书发行人,应于图书出版前,将印本或稿本呈请教育部审定”;送审样本,“由教育部将应修正者签示于该图书上”,发行人应即照改,并“呈验核定”;凡经审定合格的教科书,每册书面“载明某年月日经教育部审定字样”;各省组织图书审查会,“就教育部审定图书内择定适宜之本,通告各校采用”。
只从规定上看,政府似乎对教科书的审查极为严格,但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混乱中,这些规定很难得到严格执行。例如,1905年山东学务处的宋恕上书,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皆直言我太祖庙讳,肆无忌惮,乃至此极,按之律例,實属大不敬之尤。方今孙文逆党到处煽乱,此种大不敬之教科书实亦暗助其势力”,因此应从严禁购。商务
印书馆的“此等”教科书还可以出版流通,也从反面说明,政府对教科书的控制并非想象的那样严格。更重要的是,清末民初均确定了教科书由民间编写的制度。由于教科书是各书局的最大利源,迫使各出版社要在教科书上展开竞争,其中内容的竞争是很重要的方面。追求利润的产业意志的推动,使各书局很难完全遵从政府对内容的限制——求新求变是市场的要求,特别是对民营书业而言。据研究者分析,在光绪三十年左右,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民营出版业,1906年6月上海书业商会出版《图书月报》第一期时,光是加入书业商会的书局就已经有22家,在同年学部第一次审订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时,共审定102册,其中由民营出版业发行的有85册。民间出版机构本身就代表民间文化力量的崛起,它更多地受利润的驱使,因而想方设法突破政府的各种限制。因此,民营出版本身就对专制文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它以一种隐性力量颠覆着传统文化的霸权,这一点在清末民初的国文教材中能清晰地看到。
从教科书内容上讲,清末的小学教科书,已经开始照顾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在小学教育上的不同:西方是“其为道也,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中国则不然,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因此,梁启超建议将儿童的应读之书分为七类: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维新派的教育主张,再加上当时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对中国最早出现的教科书影响很大,如我国第一套自行编辑的《蒙学课本》(以前多是转译日本教材),在编辑大意里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