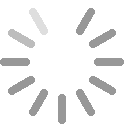教育投入: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公

2月初,国家教育部发布消息称,将成立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这个教育投入占GDP份额的硬性指标,自从1993年被写入《中国教育发展纲要》后,至今已近20年,仍未兑现,两次信誓旦旦的公开承诺都落了空。
2010年,中央政府在制订未来10年教育发展纲要时,4%又被写入了最终文本,承诺要在2012年也即本届中央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实现目标。“这次不能再言而无信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说。
国务院似乎也动了真格,早在去年8月,财政部就下发了详细的实施细则,提出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投入教育等强硬的财税政策。
与过往每次承诺不同的是,随着GDP多年高速增长,今天,从中央政府到大部分地方政府,大多财政充盈,以至于每到年底各部门往往要集中突击一下,才能把手里的钱花出去。可以说,只要中央政府真正下了决心,完成4%的目标看起来并不难。
对于中国教育来说,这个极具象征意义指标的完成,也将意味着经费短缺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但同时,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马上会扑面而来。过去的10多年里,被总量不足掩盖着的是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而这或许才是中国教育更为本质的问题。
4%的价值
在中国公共财政决策史上,教育投入占GDP的4%这个指标恐怕是最著名的一个争议了。其最初源于198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等一批人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各领域忙着制订长远发展规划,但对于决策高层来说,政府教育投入究竟应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比例,并没有可靠的决策依据。
厉以宁等人经过两年多的深入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按照邓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标准和当时的实际汇率计算,到2000年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应该是3.87%。后来又经各部门协商,最终写入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目标是到2000年末达到4%。
过去的10多年里,目标被一拖再拖,几乎每年全国“两会”上,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们都会追问此事,而财政部的答复同样也是多年未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太低,一位财政部原部长就曾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低。2010年初,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制约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提高。
不过,在朱永新看来,除了这些之外恐怕还有统计数据本身的问题。“一方面GDP的统计有水分,另一方面,教育经费本身的统计办法也不可靠。”朱永新举例说,政府本身很多经费的投入事实上并没有纳入,比如各级党校经费、公务员、国企员工培训经费等等。
有一年全国“两会”,记者碰到一个GDP过万亿省份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时问他,教育投入4%的目标在该省何时能实现?“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他直截了当地说,并给记者算了笔账,该省GDP过万亿,但省级可支配财政才800多亿,如果按4%给,那就是400多亿,一半都给了教育,其他部门怎么办?当记者追问“是不是经济结构和GDP水分的问题”时,他叹了口气,“这个不能说”。
在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也存在类似问题,广东“三来一补”类型的加工企业多,产值也很大,但和税收的关系却不大,“我们只是领点加工费,真正的税收是在出口到欧美市场那边形成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让广东也按4%来实施,显然不公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在税收占GDP比重不大的背景下,地方财政中的大部分又被上缴给省和中央去补贴欠发达地区,怎么去兑现4%的承诺?
不过,在教育界看来,财政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说法并非全部站得住脚。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各级政府存在庞大却又含混不清的各类预算外收入,使得纸面上的财政数字并不能代表政府的真实收入,否则怎么解释每年庞大却又持续高速增长的政府“三公消费”以及年底突击花钱的离谱现象?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就认为,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是对价值的分配,即对事物重要性的排序。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钱总是不够花的,关键看你怎么花。一个普通农妇可以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供养子女上学;与之相反,许多政府会认为修大马路、大广场是更重要的,这反映出教育的贫困首先是价值的贫困这样的基本事实。
过去的将近20年里,经过财税体制的多次调整,从中央到地方,财权与事权倒挂,收入大部分被逐级拿走,而像办教育这类事权则一级一级往下压,到最后由县级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缺钱的县级政府只得号召人民集资办学,农民们除了交粮纳税,还要集资办教育,然后,再花钱把自家孩子送进自己集资办的学校里去读书。
可以说,在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财税体系下,正是亿万国民额外的教育投入,让中国实现了所谓的“穷国办大教育”。中华文明中重学兴教的传统,在特定阶段的政府责任退场时,让文化心理的惯性维系了教育的兴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中国并不完全透明和精确的财税体系中,4%这样一个硬性指标,或许并不具备多大的财政考核价值,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政府的信用和责任。
总量充足之后
2012年是本届中央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4%的目标,似乎也下足了决心。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为了保证充裕的资金来源,财政部废止了1986年起对外资企业免征教育附加费的优惠制度,内外资统一按“三税”实际缴纳税额的3%征收教育费附加,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此外,从2011年1月1日起,各地方政府要从土地转让收益中提取10%,用作专项教育资金。
在地方政府层面,多年来发达省区、中央政府和不发达省区之间围绕考核标准、转移支付规模的不断扯皮也暂时停息了。在1月份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各地政府几乎都做了明确的承诺,甘肃、陕西等西部省份按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执行,而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则大都选择抛开“4%”的考核办法,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目标,大都在20%以上。这些承诺如兑现,到2012年底,完成4%的总体目标绰绰有余。
如果按照201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计算,那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将超过2万亿,从总量上讲,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但是,依据国际通行的评价体系,对于教育财政充足性的评价,有绝对充足和相对充足的概念,一般来说,对教育体系中的弱势群体是否给予了合理的财政支持,是比总量更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中,这一点尤为突出。当中西部很多基层政府仍旧陷在多年前的“普九”债务泥潭中无法自拔时,东部发达省区事实上大部分教育投入已经达到了国际通行的标准,进一步的财政投入去向才是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更重要的作用是要促进教育公平,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受到教育,实现社会目的、价值观的社会化,特别是使社会下层人士的子女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他们不利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实现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可是在中国传统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中,很难看到配置过程中的效率及公平。
在基础教育领域,过去的10几年,在东部富省和西部穷省间,教育水平的巨大落差,除了人们的现实观感外,学界的各类研究报告都清晰地显示出,二者之间在教师工资、生均经费、居民教育负担等最重要的几个公平性指标上的差距都逐年拉大,生均经费一项更是差距高达数十倍。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一直引起发达省区的怨言,另一方面在教育鸿沟的扩大面前,又显得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