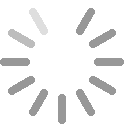永不终结的“修行”
一
将教育类书籍列为自己的必读书目是近几年的事情。
一为纠偏、戒躁。由于被一套完全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话语系统打蒙,加上当时的《教育学》、《心理学》、《语文教材教法》也确实存在注水现象,使得很多一目了然的道理,被说得臃肿不堪,且与教学实践隔着好大一截,所以读师范那会儿疯狂背诵,梦呓似的将之对付及格后,便不再理睬它们了。这种因一两本书不合己意而否定整个门类书的偏激与浮躁,自然难以登堂入室。
二为验明正身。教师是专业人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中,教师被列入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工作者”的类别中。可是扪心自问,与教育圈外的人士相比,自己对教育专业的知识和技术,真的很精、很熟吗?心虚得很。都说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可是对中外教育史,本学科教育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不甚了了,又谈何融入与创新?
2012,我读的教育类书籍主要有:叶澜的《教育概论》,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还有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
知道叶澜老师是从她的“张扬学生的生命活力”说开始的,系统地阅读她的著作则始于《教育概论》。
叶老师的理论紧盯教育实践,努力不为空言,所以读来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叶老师指出:“只有真正涉及学生真实生活中的道德情感、意志与行为习惯的发展时,只有直面学生发展中的困惑和需要时,才能产生真实的效果。”对少年期的教育,叶老师坦言:“既不要折断他的翅膀,也不能任其乱飞,而是顺势助一臂之力,送他上青天。”说得多么切实,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啊!
《外国教育史教程》语言平实,内容厚重,可以说疗救了我的孤陋寡闻,读后真的有《庄子》中那位河伯见到东海之神时的感喟和汗颜。
我不知道遥远的古代希伯来人竟然已经将教育和民族的盛衰联系到了一起;更不知道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的阿拉伯帝国在完成统一之后,立刻重视起了教育,视宣传正道、提倡学问的学者是仅次于上帝与天使的人,知文识理的战俘可以立刻获得自由,从而使文化科学的成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峰。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灵魂转向”,看到真理、本质、共相,认识最高的理念——善。各种知识都有实用价值,但这不是终极目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伦理美德就是中道,中道在两种过错之间,一方是过度,一方是不及。道德品质是被过度和不及所破坏的……
真是字字珠玑,能引发人无边的联想和深度的沉思。我想:当下的老师若能发自肺腑地接受这些可贵的经验和思想一点点,并力所能及地化用到实践中,中国的教育也不会如此重技轻道,重智轻德,导致教育活动像刮台风,根本无法渗透到心灵的土壤中去。
《当代教育学》笔墨俭省,内容浩瀚,有点像教育的百宝锦囊。一书在手,窃以为无论是对教师理论素养的积淀,还是对教育教学的启悟,都是极富针对性的。与叶澜老师的《教育概论》相比,该书“独识性”的东西不多,但是对各家教育教学理论的梳理与介绍,层次感极强。想要快捷地一窥教育的堂奥,阅读该书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
有段时间一味地读教育类书籍,竟然产生了语言干涩,思想艰涩,情意枯竭的感觉,于是我又赶紧阅读了文学理论类著作,诸如徐葆耕的《西方文学之旅》、刘再复的《人文十三步》、余秋雨的《艺术创造论》、王乾坤的《文学的承诺》,还有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徐葆耕先生是我敬仰的学者,他的视频和著作都是被我当作“宗教”一般信奉和膜拜的。同样是涉猎公共知识,但是一经先生笔墨的点染,那些知识立刻显得个性独具,丰满多姿。如果用“生命融合”的美学标准来衡量,先生的著作当之无愧。说他是拿命在写作,字里行间满浸他情感的汁水,闪耀着智慧的光辉,一点也不为过。
有人说“拜伦是卢梭的后代”,先生这样加以辨析:“拜伦确实从卢梭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但卢梭在敌人的恶意中伤面前那种近乎软弱的善良却是拜伦所不能接受的。拜伦对敌人有一种钢铁般强韧的、深入骨髓的憎恨,而这种憎恨恰好构成恶魔派的主要特色。”对司汤达的“法兰西精神就是献媚”一说,先生马上指出:“向人献媚,这是人生依附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自身缺少独立性的必然表现。”
甚至连章节标题的设置,也体现了先生无与伦比的独创,比如在“英雄性格应是冷酷和机敏,最无用的是温情”这一节中,他深度分析了巴尔扎克的诸多作品;在“金钱与爱情:关于通奸故事的模式”中,他一口气分析了《高老头》《弃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德伯家的苔丝》《美狄亚》《白痴》《嘉莉妹妹》近20部作品。思想之灵动、视野之开阔、论述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
刘再复的《人文十三步》真是上等好茶,需要慢慢细品。快喝,无法得神、得趣;多喝,又会神醉,目迷。读刘先生的著作,多在黄昏与傍晚,躲进小屋成一统,让宁静的气氛氤氲全身,然后听他娓娓道来,着实起到了意静神闲的作用。
刘先生也是一位严格忠于内心体验的人,大家熟知的人物形象经他一说,立刻会新意迭出,深度别具。譬如评论《红楼梦》里的晴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是平民中具有贵族精神的典型。说黛玉之死,并非死于几个“封建主义者”之手,而是死于共同关系的“共犯结构”中。“结构中人”并非坏人,恰恰是一些爱她的人,包括最爱她的贾宝玉和贾母。
刘先生还是一个很会分类的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学、文化现象,经他一分类,立马各归其位,清清爽爽。如文化中的“原形”与“伪形”;隐逸观念中的“自我放逐”与“放逐国家”;生命美有4个维度:质美、性美、神美和貌美。我和厦门一中苏宁峰老师的对话体论文《祛魅了,才是真心英雄——谈“伪形文化”对新解课本中人物形象的启示》,正是受先生思想启发的产物。
《艺术创造论》、《文学的承诺》和《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这3部专著至少具有下述两个共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