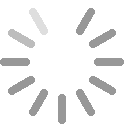天路幽险
这条道,一条夹在荆棘与巉岩间的幽险古道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过,年复一年枯枝败叶堆积得太深厚了,我听见脚下正咔咔裂响,踩在上面的感觉又厚实又空洞,这是一种特别古怪的感觉,我还从未以这种方式走进历史。其实还有另一条路,那是一条捷径,一溜烟就可以接近我的目标,但那是一条偏离了历史真相的路,而我想找到一种更真实的感受。
一座书院是必然会出现的。当阳光在树最多的地方暗下来,古榕灰绿色的浓阴连同逶迤山影,扑面而来,一下笼罩了我,恍惚间有些辨不清今夕何夕。而为这浓阴长久笼罩着的,便是这毓秀峰下的一座书院,它仿佛一直在这寂静的阴影中等待,等待某一个时刻露出它的本质。在它成为一座书院之前,其实是一位北宋士大夫的别业。别业主人郑安道,一作郑乾道,福建尤溪本土人氏,宋神宗熙宁年间进士,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此公自号义斋,这别业名曰南溪馆,也叫义斋馆舍。而它能够载入史册,其实又与它真正的主人无关,却与一次非凡的诞生有关。北宋末年,一个叫朱松的尤溪县尉一度寄寓于此,而在朱松寓居于此时郑安道已逝世多年,此公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在家乡营造这座别业,唯一的意义就是为了一个圣人的诞生而准备的。在他死后多年,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午时,一个即将被命名为朱熹的婴儿,在这馆舍西厢房诞生。而这还不是它最后露出的本质,还得等到朱熹逝世数年之后,宋理宗才将这座南溪馆或义斋馆舍赐额为“南溪书院”。
在后世眼里,一座书院就是一个圣人的故乡,但严格说,这里只是朱熹的诞生地,追溯其祖籍,则为徽州婺源。尽管朱熹并非在婺源降生,那里却有着更神奇的传说,在朱熹降生的那一刻,婺源南街的一口古井溅出一片如太阳出世的彤光,持续三日不绝。老乡们说,这是天降祥瑞,必出贵人。又据说,朱熹降生时,脸庞右侧有七颗小黑痣,排列如北斗七星。如果这么多黑痣长在别人脸上简直是破相了,但若长在一个圣人脸上,那就是神奇的天相和星象了。
朱松为宋徽宗朝进士,这一榜进士中日后最有出息的便是一度“总中外之政”的南宋主战派领袖张浚。而朱松在同年进士中算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入仕后,一直辗转于政和、尤溪等地担任县尉一类的卑微官职,据说因“不附和议”而遭秦桧打压,活了不过四十六七岁就病逝了,也可谓是遭秦桧迫害致死,这也在朱熹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秦桧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像朱松这样一个芝麻官,日后能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只因他是一个圣人的父亲,而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与民间传说,命定的也只能与他那必将成为圣人的儿子联系在一起。一个最有名的传说:朱熹还在母腹中孕育,朱松曾求人给自己卜了一卦。卜者曰:“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这恐是后人附会,自然是不能当真的,但朱熹日后能成为一个人格高尚、智慧高超的圣哲,则又是历史事实。
眼前,这一座看上去古朴庄严、俨然如庙堂般的书院,早已被岁月篡改得面目全非,但朱熹手书的四副板联据说还是真迹:“读书起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这也是所谓圣人的境界了。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圣人,除了天赋,必然还需要各方面的造化,而风水与家教尤其重要。南溪书院内那半亩方塘,据说还是当年的模样,朱熹幼年在此读书,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看就知道,朱熹诗中那半亩方塘早已被后世扩大浚深了,还建起了一座像模像样的活水亭。想象一个孩子能在明媚的阳光与波光中度过自己的童年,也是他的福分与缘分了。朱熹一生信仰的理学或道学,从其开创始祖周敦颐开始,对风水就是特别看重的,这样的风水对他的品性情操必然会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陶冶。又从家教看,朱松在仕途上没有什么出息,但据说也很有文才。朱熹幼年受教于父,这也是他人之初的精神源头。相传他四岁时,朱松一手指天告诉他:“这是天。”朱熹却奇怪地问:“天的上方有什么?”一个童子的天问让一个父亲大惊,他瞪大眼睛看了这小子许久,却没有回答儿子的天问。天的上方有什么?谁知道呢?
朱熹在义斋馆舍度过的时间并不长,对于他,这里只是一条路的起点。童年时代,他几乎一直追随父亲辗转于宦途,一直在路上。而他还将继续演绎他的神话或童话。史载,他八岁时便能读懂《孝经》,并在书上题字自勉:“不若是,非人也!”——若不按《孝经》上所说的去做,就不是人!这颇有点孩子气的赌咒发誓。遗憾的是,他那早逝的父亲却没有给他恪尽孝道的机会,朱松病逝时,朱熹才十岁,一说十四岁,随母定居崇安五夫里(今福建武夷山市),在穷困的家境中度过了少年时代,但无论有多苦也没有中断学业。朱松弥留之际,临终托孤,将朱熹托付给自己的三位道友胡宪、刘屏山、刘勉之代为教养,这三位道学先生都是不慕虚荣、不事权贵的高士,世称“武夷三先生”或“武夷三贤”,如果不是他们,一个寡母还真是难以将朱熹拉扯大。“武夷三先生”是朱熹在父亲病逝后的精神源头,他师从这三位师父,从他们的学养中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也为日后成就一代大儒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和精神底色。
在苦读的同时,朱熹也有一份甜蜜的收获,恩师刘勉之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刘勉之一生不仕,“结草为室,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但他的得意门生兼女婿朱熹却不愿放弃仕途。随着一个少年渐渐长大,就该背着包袱上路了,这条路,是一个士人走向士大夫的必经之路,朱熹一路走得相当舒展和顺畅,史载朱熹“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但他可能未登甲科进士榜,若要入仕,还得等待两三年。三年后,朱熹被朝廷授以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就在赴任途中,他拜见了程颐的二传弟子、“南剑三先生”之一李侗。为表诚心,他步行数百里,一路从崇安跋山涉水走到延平。道学家常以这种方式磨练自己的心志,也常以此来考验别人的诚心,如“程门立雪”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事例。对于跋涉数百里前来拜师的朱熹,李侗也非常欣赏,他认下了朱熹这个弟子,并替他取字元晦。朱熹字元晦,并非父亲之命,而是源自师门。
朱熹拜师李侗还只是在正统的理学上刚刚入门,这和他在仕途上的进程是一致性的,主簿也只是仕途的入门之官。朱熹在同安主簿这个卑微的官任上倒也显得澹然而有耐心,只因他内心里还有另一种追求。同安离泉州相距百余里,他父亲宦游过的安海恰好处于同泉之间,朱熹时常于泉州各地寻幽探胜、求贤访友,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他都要寻访父亲生前的遗迹遗事,和当地的鸿儒名士谈经论道,如此一来,安海就成了他最早传播理学的一个地方。同安主簿任满后,朱熹的仕途功名之心更淡了,乃请求辞官,从此潜心钻研理学,四处讲学。此时,他从周敦颐的“太极即天理”、二程“存天理,灭人欲”的思路轨迹中,融合道学、佛学、儒学思想,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越他的宗师李侗,中国理学的一个最大流派——“程朱学派”,将在他手中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