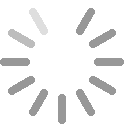不独子其子:五四前后关于儿童公育的争论
〔摘要〕 清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部分思想激进的读书人放弃了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传统社会模式,转而构建不独子其子、不独亲其亲的大同社会,即儿童出生之后,交由公立机构养育、教育。这样,男女双方只需生育而无抚养、教育的责任。他们相信这不仅有助于实现教育平等和社会的根本改造,而且可以藉此将妇女从育儿的责任中彻底解放出来。不过,这一事关儿童的讨论,却忽视了儿童自身的诉求和人类对亲情的基本需要。
〔关键词〕 儿童公育;不独子其子;教育公平;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186-08
就一般的生活伦理而言,近代可以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内忧外患造成的焦虑心态中,传统的经典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淡出,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1〕而人们对“未来”的设想不再是回到“黄金古代”,而是已知的美好“未来”。〔2〕在各种新奇的、被建构的未来之中,有一部分激进的读书人从基本的社会制度以及人伦关系的角度反思家庭的存废问题,以想象为基础构建起一个无家的未来社会。如康有为就主张,“人皆天所生”,故“人人皆直隶于天”。欲至太平,“舍去家无由”,并由人人共设一个“公政府”,此“公政府当公养人而公教之,公恤之”。②
按照康氏的设想,无所谓父母的儿童自出生就在公共的机构中成长,历经公立育婴院、公立怀幼院、公立蒙学院、公立小学院、公立中学院、公立大学院完成教育,成为独立的劳动者。且这样的成人可以说是一个“公人”,其“养生送死皆政府治之,而于一人之父母子女无预焉”。〔3〕为了使每一个儿童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和衣食住行,主张废除家庭,由政府安排每个人成长的轨迹。
这样的设想在今天看来也相当超前,但在清末民初却为不少读书人所分享。1920年春,恽代英和杨效春就曾在《时事新报》上反复争论儿童公育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前者极力支持,而后者坚决反对。恽代英和杨效春当时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此后仍保持通信。因此,这次辩论可以看作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张东荪就认为这次辩论中“双方的话都有价值”。〔4〕
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或因各种原因多半关照论战中支持儿童公育的恽代英的言说,而忽略张东荪所谓那亦有价值的另一方。既存研究大体上正面评价儿童公育的主张:或从平等的角度肯定儿童公育〔5〕,或认为儿童公育符合教育社会化的趋向。〔6〕研究者似乎确信儿童教育社会化是“进步”的象征,而忽略过分社会化的公育对儿童心理、社会组织以及人性本身的挑战,及其可能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本文尝试将双方观点都放在清季以来对社会组织、儿童教养方式进行反思的语境中进一步考察。
一、儿童公育:不独子其子的新解
对思想激进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构建的“未来”中并不存在家庭。这看似反传统的主张或正是受到了西方以及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启发。严沁簃观察到,“今之持论过激者欲举家庭根本推翻之”,而支持柏拉图所玄想之儿童公育。〔7〕任开国也指出,“儿童公育这个名词,并不是现世才有的,在两千多年前,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也就主张过”,不过在柏拉图的时代无法成为事实,而现今已经由理论变为事实。〔8〕
或许儿童公育正是“不独子其子”的一个新表述。《礼记·礼运》开篇即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9〕康有为在撰写《春秋董氏学》时注意到《礼记·礼运》篇。〔10〕康氏在《礼运注》中称:“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11〕王汎森指出,《礼记·礼运》篇本是“一篇两千年来不被学界主流突出表彰的文献,被康有为推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其中的乌托邦意味,早已超过它原有的脉络及传统的诠释。”〔12〕整体而言,儿童公育或可以被看作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与西方先哲柏拉图政治思想的一个奇特组合,带有较强的乌托邦色彩。
此后,不少政治立场对峙的读书人都曾试图沿此思路诠释儿童公育。宣扬家庭革命的《新世纪》杂志曾刊出一篇来稿,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同废除家庭划上等号。〔13〕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未来也实现了公养、公育,“斯时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之束缚,无名分之拘牵,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者,斯不亦大同社会之权舆欤?”〔14〕曾任孔教会总干事的陈焕章认为,天下为公即指“破除家界,直隶于天”,并据此实现“礼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15〕孙中山也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启发,致力于建设“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世界。〔16〕邵力子则相信儿童公育就是实现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途径。〔17〕若以天下为家、天下为公分别代表了家庭存废不同时代,那么这也对应着“各子其子”与“不独子其子”的对立。〔18〕
无家庭的未来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对父子关系的认识。管际安认为,“父母儿女的名词,不过人类中的一个符号,是教养者与被教养者的口头契约。有了这种契约,教养者与被教养者便照此一方履行义务一方享受权利。”在他看来,“骨肉间的狭义感情”应化为“社会的广义感情”。〔19〕曾在清季倡导女子家庭革命的柳亚子也期待“将来大同世界”中可施行“自由恋爱,儿童公育,连父母妻子的名义都没有了”。〔20〕
儿童公育的言说挑战了父母在儿童教养中的主导地位。孩子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逐渐超越其家庭成员的资格。陈顾远主张,“一个人生下一个孩子,不必管他是谁底种子,反正是社会上一个‘人秧子’,就抱给公家去抚养。在公家方面,也不必问这孩子是谁生的,只认定是社会上一个人生的”。〔21〕管际安则试图调整生育与养育的承担者,主张“公家”更多地参与到养育之中。盖“无论什么人所生的儿童,并不是为他自己生儿子女儿,是替社会上生儿童,并不是享权利的,是尽义务的。”〔22〕在管氏看来,人们既然替社会尽了生育的义务,就不必让父母承担教养之责任。有位作者也呼应此说,“原来儿童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父母的养育儿童,也不过是代社会养育。”〔23〕甚至有人宣称,儿女“乃是社会的儿童”,故为“社会所有”,则“儿童的教养,当不仅是其父母的责任,实在是社会的责任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