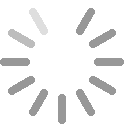调适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回族民间教育
摘要:纵观中国回族教育,其发展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政治环境、民族内部的主体性与文化自觉息息相关。相对国家主流教育,回族教育始终属于少数民族民间教育,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宗教性、民间内敛性与调试工具性。回族教育通过自身与时俱进的调适和发展,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始终起到积极作用。当下云南回族民间教育的调适与发展,表现为不同层次民间教育文化圈的回族文化再生产。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力量和国际环境对中国回族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为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回族教育危机,应加强回族民间社团的组织与机制建设,全面开展回族民间教育体制创新,积极谋求社会化的民族教育渠道和方式。
关键词:全球化背景;回族民间教育;调适;发展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3—0129—07
全球化研究理论(超级全球化论、怀疑论和转型论)对教育的关照各有不同,形成两个主要的派别: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追求一种“工具性教育”,认为教育体系的重点是发展年轻人应对并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能力;而全球化的批判者认为,在文化霸权主义下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的全球化进程,没有体现自身的教育价值,也没有关注本地区的真正教育本质。目前主流形式的工具性教育远离了现代教育的首要目标,体现出狭隘的个人主义。以上两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观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极不利于像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公民教育和国家认同。
中国回族大分散小聚居,围寺(Masjid)而居的哲玛提(Jamaat)作为回族社会的基层人群单位,是人们理解回族社会的窗口。作为维持回族边界的重要文化机制,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其民间知识教育传承网络,在回族超越以哲玛提为单位的地方性知识与地理空间的区隔,体现民族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回族正是通过一个个哲玛提社群的民间教育与民族文化再生产,不断进行个人、集体及整个民族的社会化调适与发展的。中国回族民间教育在不同时代受到中国主流社会、伊斯兰世界乃至非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教育思潮的巨大影响,一方面秉承伊斯兰教教育思想,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教育具有很多同质性;另一方面,又在谋求发展的不同时代背景下不断调适和建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教育体系。可见,回族民间教育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宗教性、民间内敛性与调试工具性。这种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尤为突出。
云南是中国回族人口较为集中的省份。自元代至明代,云南回族文化教育十分发达,成为与陕西、金陵(南京)、山东并驾齐驱的中国伊斯兰教四大文化教育中心,在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近代,云南因成功创办新式学校,组织中国回族社团,出版中国回族书籍报刊,培育著名学者和阿洪,而在中国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云南回族通过积极推进民间教育的创新发展,在促进中国回族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提高中国回族公民素质、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云南调研资料,就全球化背景下回族民间教育的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一、回族教育的历史变迁
(一)传统经堂教育:宗教文化传承
蒙元时期,中亚、西亚的大批穆斯林进入中国。元朝由于回回人政治地位优越,国家设立“回回国子监”教授“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其可被视为公办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侧重语言文字)。其中经师和学者多在礼拜寺中任掌教或在穆斯林中从事传教活动,被称做“答失蛮”,他们是回族先民早期民间教育的倡导者与传承者。明中叶之前,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主要依靠家庭的言传身教。伴随穆斯林中国本土化进程,多数穆斯林使用汉语言文字,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无法实施。明中叶以后,中央王朝一度采取海禁政策,国内伊斯兰教面临生存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一批穆斯林有识之士,倡导发展宗教教育,振兴伊斯兰教。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陕西胡登洲(1522—1597)所创立的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宗教教育本土化的开端。胡登洲在赴麦加朝觐的回国途中游历并考察伊斯兰国家的教育状况后,深感中国“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于是“慨然以发扬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开始在自己家中设帐免费讲学,后转移到清真寺内。这种伊斯兰经堂教育(madrasah)和中国私塾教育的初次结合,为中国回族民间教育开辟了道路,并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制度。之后,山东、江浙、湖广、云南、广西等地也兴起了较大规模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的倡兴,是伊斯兰教教义、经籍学说在中国内地的一次普传,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开始。随着经堂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回族民间教育的初高等教育形式逐步分离,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逐渐形成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种学制。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他在昆明兴建了永宁、南城等12座清真寺。当时昆明地区回族穆斯林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围绕着这些清真寺已经有所发端,至今云南各地回族民间保存着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古语就是明证。
(二)“以儒诠经”:中国化调适
明末清初,一批穆斯林宗教学者“以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籍为蓝本,吸取中国宋明理学的思想,运用儒家学说的概念、范畴、语词与表述方式,著书立说,解释经籍,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史称“以儒诠经”。其从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王岱舆(1584—1670)开始,到清末汉文译著学者马联元(1841—1903),共分为三个阶段,前后持续200余年。经堂教育与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展,加速了伊斯兰文化本土化进程。云南学派作为四大代表学派之一,首倡“中阿并授”,同时吸纳南京汉学派倡导将伊斯兰教著作译为汉文,学经习儒的思想,开传统经堂教育向新式经堂教育过渡的先河。据清代赵灿《经学系传谱》记载,早期陕学经堂教育的一传、二传弟子里已有滇籍回族马寿清(普洱马)和黄巴巴、蔡巴巴3人,3人伊斯兰文化造诣精深,在云南伊斯兰教育史上颇负盛名。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回族伊斯兰经学大师马注与马德新两人成为云南伊斯兰学派的先驱和奠基者。云南回族穆斯林的经堂教育盛极一时,玉溪大营,河西(今通海)纳古,华宁婆兮(今盘溪)等地,成为清代云南伊斯兰经堂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文化中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著名阿洪马复初朝觐回乡,先后在临安(今建水)回龙,新兴(今玉溪)大营设帐授徒,“四方从学之士,星列云集”。从此两地成为云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心。中国回族民间社会的知识精英表现出经书两通、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糅合的特点。